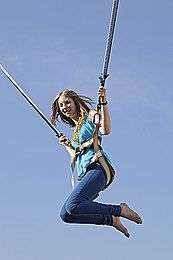2017年9月21日下午
2020-03-10 00:33:36 双城汽车网
[编者按]:莫娜·奥祖夫(Mona Ozouf)是享有国际声誉的法国历史学家,她和弗朗索瓦·孚雷(Francois Furet)一起开创了法国大革命批判史学。2017年9月21日下午,由商务印书馆主办的莫娜·奥祖夫“革命·女性·文学”三部曲新书对谈会在涵芬楼书店举行。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刘北成、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杨念群、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倪玉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海青围绕莫娜·奥祖夫的《革命节日》、《女性的话语》和《小说鉴史》进行了一场火花四射的精彩对谈,对我们理解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对中国的影响、女性主义等话题都有所启发。访谈全文分上下两篇刊发,此为上篇。
莫娜·奥祖夫“革命·女性·文学”三部曲新书对谈会现场照片。
刘北成:我先做个引子。约三十年前,在纪念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的时候,中国学术界和莫娜·奥祖夫不期而遇。那是两种历史反思的相遇。
当年,孚雷和奥祖夫等一些法国学者上承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史学提出了所谓“修正主义”的解释。1988年,孚雷和奥祖夫共同主编了一部《法国大革命批判辞典》,凝聚了修正派的研究成果。到了1989年,法国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在法国革命史学的专业研究领域,占据主流的依然是正统的左派学院派例如索布尔,但孚雷派的观点赢得了媒体。
对于这批修正派学者,有各种不同的评价。有人认为他们是法国大革命的否定派,甚至认为他们是右派。奥祖夫本人否认这种看法。她表示,他们不是右派,而是左派学者中的修正派。不仅孚雷和奥祖夫,近年读书界所关注的托尼·朱特也是这样的学者。怎样看待左派学者里出现的修正派?这个现象很有意思。
1989年,在北京举办的法国大革命200周年史学研讨会也恰处于中国八十年代的反思高潮。索布尔出席这次研讨会后,感到吃惊。他对我国著名的法国史学者张芝联先生说,中国的史学家都变成了“热月党”!在这次研讨会上,有外国学者也介绍了法国的大革命史学修正派的信息,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
从那时起,中国知识界和孚雷、奥祖夫等之间就有了某种精神联系。但是,可以说,一直似曾相识却又从未相见。近年来,我们引进翻译奥祖夫的三部曲以及正在翻译《法国大革命批判辞典》,希望能够让中文读者与他们形成一种真正的对话。
第二、关于莫娜·奥祖夫。莫娜·奥祖夫是19 1年生人,今年已经86岁了,依然健在。莫娜·奥祖夫生在布列塔尼,在法国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地区。但是,莫娜·奥祖夫出生在一个教师的家庭,她的父母都是中小学教师。她4岁的时候父亲去世,跟着母亲和外祖母长大。奥祖夫基本上是在一个知识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到1954年,也就是2 岁的时候,她考上了巴黎高师。这是法国最精英的学校,萨特、波伏娃、福柯等都毕业于这所学校。
莫娜·奥祖夫在1955年结婚,改姓奥祖夫。这不仅仅是一桩婚姻,而且使她进入了一个知识圈子。她和她的先生,和一些知识精英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这里面包括勒华拉杜里、孚雷等。莫娜·奥祖夫后来在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工作,这是布罗代尔创办的一个介于建制内和建制外之间的学术机构。
莫娜·奥祖夫是一个文雅的知识女性。文如其人,看她的作品,我们会对此有比较强烈的感觉。她基本上是在和知识精英、和知识精英的文本打交道。这也决定了她的态度、品味。中国会有越来越多的读者,对她的作品产生精神上的共鸣。
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在布罗代尔的倡导下,强调打破专业畛域,进行以“问题”为导引的“总体”研究。奥祖夫的研究也体现了这个特征,研究领域涉及史学、哲学、文学、教育学。我们认为她的著作有几个特点:
第一,这些著作在学术上都有开拓性。莫娜·奥祖夫是孚雷的合作者。不过,奥祖夫更偏向文化研究。譬如,《革命节日》被公认是新文化史研究的开拓性作品之一。这种开拓性奠定了莫娜·奥祖夫在学术上的地位。
第二,这些著作具有可读性。她的作品散落着许多睿智的见解,而且文字优雅考究。《女性的话语》和《小说鉴史》的中文译文也非常漂亮,也很传神。所以,读这些作品会有一种精神上的愉悦。
第三,这些著作具有话题性。她这三本书所谈论的问题是法国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但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也会有真切的感觉。比如说革命节日这样的话题,革命和节日如何联系起来?在革命之后,我们进入到了一种什么样的节庆?《女性的话语》这本书里,她给了我们十幅知识精英女性的肖像素描。她画得像不像,对于一般读者来说,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里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法国知识精英女性的思想和人格。《小说鉴史》讨论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和解历程,尤其是后革命时期市场主导、金钱至上环境里的社会转型,那些小说提供了各种镜鉴。
奥祖夫的作品中有许多精彩的文字。为了给大家更直接的感受,我来朗读几段饱含人生沧桑体悟的文字:
正如夏多布里昂所言,这些新时代的老人是世界上落伍的人。他们看到自己周围不仅一些人不在了,而且一些观点也消失了。从此之后,感到身处异国他乡。有人将为这种内部流放付出沉重的代价。(成为故土的异乡客、内部的流放,这种感觉非常痛彻。)
年轻的革命者也碰到了老化的问题,这就是法国大革命的老化(指后来者的大革命理想已经落伍)。所有人都认为向他们开启了大门(历史的重复错觉),实际上,当前也有着很悠久的历史。
在这段时期(十九世纪中期),每个人都在不声不响地做着自己的事,保皇党人变成了自由派,自由派变成了民主派。在这个善于不动声色地乔装改扮的时代,人人皆是过客。
这样的文字不仅触摸历史,也触摸内心。
莫娜·奥祖夫(Mona Ozouf)。
杨念群:刚才刘老师非常有诗意地表达了自己的心绪。大家知道北成兄曾经翻译过许多法国名著,从福柯的《规训与惩罚》《疯癫与文明》到奥祖夫的《革命节日》,刘老师的翻译文字很传神,很好读,实际上是带着诗意、带着自己的感情来理解作者的用意的。他刚才念的一段文字,实际上是一种个人心境的自白,同时也反映出他把整个翻译的对象融化到自己生命里去进行体验的意图。只有通过这样的体验,才能实现环境、译者和翻译对象融为一体的目标。
大家刚才也提到了“革命”这个话题,“革命”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永远是一个 澎湃的字眼,许多人都在革命的氛围里出生成长,刘老师的岁数比我们都大一些。但是遥想当年,我也是最后一批红卫兵,胳膊上挂着红袖标,尽管没有赶上武斗抄家的年月,却对革命那种“诗意的浪漫”和所带来的后果感同身受。
我个人认为,大多数革命充满着浪漫 ,却同时也是一种残酷诗意的宣泄和表达,里面有着非常复杂的内容。所以,对革命的评价就会出现非常多的歧义。刘老师也介绍了,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评价有很多派别。这些派别不仅是持有赞成还是否定革命的立场这么简单,许多人对革命的评价往往与他的个人经验密切相关,里面包含着自己的感情,对革命的理解也由此变得更加多元,更加复杂,也更加值得回味。
刘北成老师翻译的书我每次都非常认真地拜读过。另外两本书我还没来得及看,所以只能就他翻译的《革命节日》跟大家做一点交流。《革命节日》实际上是新文化史对革命行动重新进行阐释的一次尝试。新文化史认为,对革命不应该仅从政治事件的角度来进行阐释,而是应该把它理解为一种更加复杂的人类活动整体综合作用的结果。这种研究取向在上个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一个热潮。比如说美国林·亨特教授对法国革命的探索,从革命者的服装、仪式,甚至谣言传播等方面进行了描述,这些要素的探讨已不仅局限于一个历史事件,而是扩散到了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却又是作为一个历史事件的“革命”的组成部分加以认识的。
法国革命对于中国革命者而言会产生一种共鸣性,仿佛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有人说,中国革命的进程实际上是法国大革命的一个翻版。高毅就写过一篇文章,说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就曾在许多方面借鉴了法国革命的经验,甚至两者具有相当强烈的同构性、同质性。
《革命节日》书封。莫娜·奥祖夫(Mona Ozouf)著,刘北成 译者,商务印书馆,2017年 月。
我的感受大致分三个层次,想从我自己的角度比较一下中国和法国革命时期对节日的空间、运动、教化关系之间的异同。第一谈空间的作用,第二谈革命如何动员,第三谈革命规训方式及其如何制度化。
这本书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是,法国革命是一个社会动员的过程,同时又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空间感,当然时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所有的这些运动、所有的节日都是在一个公共空间里发生的。大家如果去过欧洲的话就会知道,在欧洲的城市里,它的广场是聚集民众进行活动、举行仪式最重要的一个地方。但是在中国,对空间的概念可能就跟西方完全不一样。实际上,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明确的一个公共空间活动领域。
中国的公共空间,最早实际上是由皇帝或由贵族来垄断的,皇帝在某个地方举行某个祭天或祭祖的仪式,但是普通老百姓是没有资格进入到这个空间的,它只是一个上等阶层举行仪式的场所。老百姓的活动空间、举行的仪式,往往是在家庭或家族延伸的空间中进行的。在某个公共空间举行节日、举行集会,这在中国是非常近代的,非常晚近的事情。当然,在农村乡间有一些庙会可以为百姓提供某种公共活动的场所,但这些场所与集体的政治行动无关,也与某种指向明确的社会动员行为无关。中国真正出现目标明确的政治运动大致应该从五四运动开始算起,这是一次真正的广场节日,通过某一个事件把大家凝聚起来,形成了一个群体运动。这个群体的活动后来不断地被诠释,不断地被加以说明,构成了它特定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含义。五四运动作为一种广场节日,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法国革命集体狂欢的一种模仿。
广场节日只有通过社会动员的形式才能构成一定的规模,比如五四运动就是经过了反对中国使团在巴黎和会上签字的群体动员之后,大家才在广场聚集起来,形成某种政治仪式,来表达自己的民族主义热情。可见,民族主义也是一个被塑造的过程。
当年梁启超写《新史学》的时候就提出了一个“塑造国民”的口号,我觉得对我们理解《革命节日》非常有帮助,梁启超的基本意思是说,原来的中国人是没有国家概念的。国家在梁启超看来是一个可以进行政治动员的巨大空间。中国人原来只有家庭概念,而没有国家的概念,家庭的空间太过狭小,只有让人们意识到“国家”这个更为广阔的空间对他的意义,才能真正获得新生。民国初年人们提倡新史学,提倡新教育,就是要使大家重新树立一个意识,敦促大家从家庭的范围里走出来,加入到一个公共空间里,通过某种动员形式,形成我们自身对国家的感受和认同感。这是当年梁任公提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路。这个思路后来果真通过广场运动的形式得以实现了。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标志性的广场节日就是五四运动。
广场运动的形式往往表现出一种革命的 、动员的气氛,并通过各种文化符号表达出来。革命仪式所要达到的动员目标都是在广场浪漫的氛围里得到了实现。
广场仪式一旦起到了动员效果之后,还面临一个常规化的过程。五四运动以后,一直到 1949年以前,国民党通过党国的政治动员体制不断使广场仪式常规化,1949年以后天安门又增加了建国游行、国庆阅兵和领袖接见群众等各个广场项目,革命节日又变成了一个凝聚政治力量、文化力量的重要手段。从空间到动员的过程来说,广场本身的历史就昭示着中国人对空间内涵理解的变化。比如我们中国人怎么样从一个相对封闭的状态逐渐参与到一个公共的场所、公共仪式活动中去就是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这个过程的形成可能会有非常复杂的原因。民族主义意识的形成是个重要因素,近代中国人通过对民族身份的重新界定,和国家意识的培养,逐渐具有了全新的群体感觉。与之相关的是,革命又是通过对国家意识的培养动员起来的。莫娜·奥祖夫在《革命节日》里面有很多细节描述了空间活动与群体意识形成的关系,比如游行路线怎么设计,有什么样的不同阶层的人可以参与进来,节日主题对群体运动的方向感有什么样的影响和调动等等,都非常有意思。我记得林·亨特在讲法国革命时曾经指出谣言是怎么样在一个具体空间里传播并如何影响到人们的言行,这些探索都是以往史学界忽略的视角。
不同的势力、不同的人群在解读革命、庆祝节日的时候,其实有着自己的目的,自己的企图,甚至包含各种复杂的动机在里面。有的人是完全出于对政治的考量,通过革命来树立他的政治权威,又有一批人仅仅把革命当做参与节日狂欢的机会。因为他平常可能没有合适的宣泄渠道,比如在传统家庭的封闭空间中也许一个人会感到压抑,而一旦在广场上参与到一个革命节日中去的时候,他才会获得一种宣泄感。
或者可以这样说,近代的革命节日提供了一种宣泄情感的新式渠道。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问题。革命节日提供的宣泄形式到底与古代社会有何不同?谁来主导这个宣泄的过程?谁来改变宣泄的方向?自我感情的宣泄和政治本身意图之间的关联性以及两者之间存在的差别,都是值得深思的话题。对于我们理解革命节日,理解法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异同而言是个非常重要的途径。
第三、广场作为一个举行革命节日的场所,对个人言行的规训和教化起着重要的作用。奥祖夫在《革命节日》这本书里也讲到了它的教育功能。在什么样的节日动员的状态下,通过凝聚群体形成合力,来指向共同的思想意识与目标。当然,革命的意识和导向,其实是一个不太容易用一种特别学术性的语言来进行描述的概念,必须在具体的历史描述过程中慢慢呈现出来。
我也曾经参加过各种各样的广场集会,我发现每个人的情绪介入方式都是不一样的。在大多数场合,作为被动员的对象,我没有那么大的政治抱负,在很大程度上是带着一种好玩、狂欢的情绪去参与到游行队伍里去的。当然,你在介入的过程之中,会尽量持有一种旁观者的感受。同时,你拥挤在人群里的时候,在在另一种状态下,可能又被规训或者被动员到一个具体的目标之中。比如说,你到一个地方,你看到一群人在做一些事,别人会出来动员,发表一篇演讲,大家本来是看客的心理,却不知不觉进入到了演讲者导引的脉络里,随着情绪被煽动起来,每个人身处游行队伍和节日气氛中时心理都会悄然发生改变。
《革命节日》不是用某一个很具体的术语、理论规定某个场景,它更像是一种情绪的自然表达。人们参与革命节日的情绪在什么地方流动、在什么地方爆发、在什么地方沉潜下来、在什么地方出现起伏,通过一种感受先要把这个氛围描写出来。这本书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尝试,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
总的来说,这本书不仅显示出法国革命的另一个诠释路径,同时也使我们联想到了自身的历史状况。我们中国也是一个政治运动大国,尤其是在民国以后,国家不断通过公众空间来调动民众的情绪和热情,参与到特定的活动中去。奥祖夫的著作对革命群体动员的形式和动员的气氛、动员的历史进程重新加以描述、重新加以定位的尝试,值得我们去加以细细品味。
刘北成:莫娜·奥祖夫近年有一本自选集,书名是《从革命到共和国》。我们翻译的三部曲也是奥祖夫自己选定的。自选集和三部曲,不仅体现了她关注的历史时段,也凸显了她的研究主题:如何看待革命,如何看待后革命时代。她特别关注历史参与者如何调和这两个主题。这两个主题有非常大的冲突、反差。但也存在着某种勾兑的可能性。我们现在也身处这样一个环境中。革命的影子还在,但是后革命时代的现实已经在压迫着我们了。奥祖夫的话题与我们的现实有某种关联。
性别问题是法国的知识精英女性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莫娜·奥祖夫在《女性的话语》里指出,法国革命之后的教育,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消除性别造成的不平等。奥祖夫说:“性别不是监狱”。这其实针对的恰恰是相反的现实或可能性。莫娜·奥祖夫作品的主题和视角都比较独特。我觉得里面包含的不仅有精英意识,同时也有性别意识。今天参加对谈的还有两位女性学者。她们对奥祖夫这位女性学者或许有自己独到的理解。
(编辑:王怡婷)
关节积液能吃藤黄健骨丸吗祛风湿消肿止痛的药材怎么治糖尿病胃轻瘫腹胀好